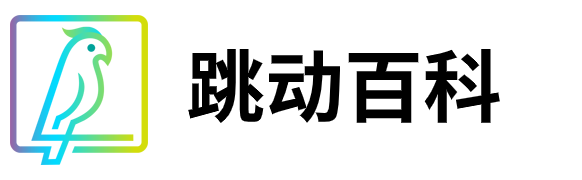博物馆科学家在2022年描述并命名了351个新物种
从到偏远地区的研究旅行,到梳理博物馆藏品中的 8000 万件物品,科学家们每年都在为这个庞大的生命图书馆增添新的内容。虽然其中许多物种已经为生活在它们身边的人所熟知,但通过给它们起科学名称,我们有望更好地保护它们。

由于地球上的大多数动物都是无脊椎动物(没有脊椎的动物),因此今年描述的大多数新物种都属于这一类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包括大约 84 种甲虫、34 种蛾类、23 种苔藓动物(也称为苔藓虫)和 13 种吸虫。还有 12 种新的原生生物、7 种苍蝇、两种来自亚洲的大黄蜂、两种来自海洋深处的多毛类蠕虫和一种科学家以前从未见过的有许多节段的蜈蚣。
但今年获得最多新物种的群体是黄蜂。共描述了85个新物种!这包括一些拥有最美丽的羽毛状翅膀的微型个体。这些微小的动物属于一个包含世界上最小的昆虫的群体。
尽管体型较小,但这些寄生蜂可能对农业很重要。这些昆虫寄生在蓟马(一种会损害农作物的昆虫)的卵上,因此黄蜂可能是重要的生物防治剂。
加文·布罗德 (Gavin Broad) 博士是博物馆负责昆虫的首席策展人,也是膜翅目昆虫(黄蜂属)的专家。
加文解释说:“新的黄蜂物种名列前茅并不奇怪,黄蜂并不是每年都名列前茅才令人惊讶。” “大量的寄生蜂使膜翅目成为物种最丰富的昆虫目,但就实际物种描述而言,它远远落后于其他一些群体。”
“明年要小心更多的黄蜂!”
今年还发现了 19 种竹节虫新品种。所有这些都来自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需要研究人员使用新收集的昆虫、博物馆标本和基因分析来揭示最初被认为是 11 种的物种实际上是 30 种。
博物馆科学家还描述了一些脊椎动物,包括来自塞舌尔的一种新壁虎、三种鱼类和七种青蛙。
其中六只青蛙是已知最小的脊椎动物。这种青蛙生活在墨西哥的落叶堆中,体长只有 8 毫米,比 1 便士的硬币还小。为什么这些青蛙进化到这么小还不清楚。
今年,科学家们不仅描述了活着的恐龙,还描述了三种新命名的恐龙的死者。两个是来自中国的装甲恐龙。其中第一个是在亚洲发现的最古老、最完整的装甲恐龙,而另一个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剑龙。这两个物种共同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重装甲群体是如何进化的。
今年描述的第三种新恐龙是一种长有细小手臂的肉食性恐龙,发现于阿根廷北部。它的历史可追溯到 7000 万年前,它提供了关于世界的这一部分如何应对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的线索。
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过去的不仅仅是恐龙化石。藏品中藏匿的一只 2 亿年前的化石蜥蜴不仅是一个新物种,而且还是科学上已知最古老的蜥蜴,将这个群体的起源往前推了 3000 万年。
在这些藏品中还有一种可怕的鳄鱼状捕食者,最初是在大约五年前出土的,在三叠纪时期可能会在现在的坦桑尼亚肆虐。
研究人员还忙于描述八种新的古代哺乳动物,主要是从它们的牙齿中得知的。在侏罗纪中期,这些新物种中的两个可能会在恐龙头顶上方的灌木丛和树枝周围飞奔。其他六个新物种是包含我们自己的灵长类动物亲属的群体的早期代表,并且在大约 3500 万年前可能生活在现在的怀特岛。
今年最有趣的化石发现之一是一只被困在乌克兰琥珀中的小甲虫,其年代也可追溯到 3500 万年前。这种特殊的昆虫被称为趾翅甲虫,现在仅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发现,甲虫化石表明,当这种昆虫在始新世晚期还活着时,乌克兰的气候一定要温和得多。
来自捷克、拉脱维亚、俄罗斯、乌克兰和英国的国际研究小组将这种新的甲虫化石描述为面对乌克兰持续不断的战争进行国际合作的表现。
“尽管目前情况如此,但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并作为一个团队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博物馆甲虫馆长 Dmitry Telnov 博士解释道。“有了这一发现,我们不会对任何同事进行分类或评判,而是向科学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保持团结和相互支持是结束战争的方式。”
有几个新的鱼化石种,还有一个有点不寻常的新物种,它以侏罗纪幽灵鲨卵壳的遗迹化石命名。在海洋中,出现了三种新的三叶虫、四种新的海蝎子和一种奇特的装甲蠕虫,它们填补了化石记录中的一个重大空白。
最后,今年描述了三种新矿物,包括一种在英国坎布里亚郡发现的具有脆性半透明蓝色晶体的名为 Bridgesite 的矿物。
许多植物和藻类也名列其中。研究人员今年共描述了 11 种新的藻类,既有化石的也有现存的,同时描述了来自南亚各地的 四种新植物,包括一种来自苏拉威西岛的植物,它长满了看起来相当可怕的刺。
Sandra Knapp 博士是博物馆的优秀研究员,参与了这些新植物物种的描述。
“尽管就生物群而言,开花植物相对广为人知,但据估计,尽管我们已经给了大约 450,000 个物种科学名称,但仍有大约 25% 的物种需要描述。不是去发现——当然,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它们发生的地方为当地和土著人民所知——我们分类学家只是给它们起个名字,让它们成为全球植物学的语言。”
“大多数植物都有多种名称,一些特定于某个地区或语言组,另一些则更为广泛,但我们创造的科学名称可以被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使用。这意味着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之一帮助扭转生物多样性的曲线。”
“毕竟,如果我们不能谈论一个物种,我们怎么能希望拯救它呢?”
免责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与本网站立场无关。财经信息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首都师范大学是211吗】一、“首都师范大学是211吗”是许多考生和家长在选择大学时经常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浏览全文>>
-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自考和统招毕业证不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的】在选择继续教育方式时,很多学生都会关注“...浏览全文>>
-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自考本科国家承认学历吗】一、“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自考本科国家承认学历吗”是许多...浏览全文>>
-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怎么样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介绍】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是一所位于北京市的全日制本科...浏览全文>>
-
【第一次电影剧情】《第一次》是一部由美国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执导的电影,于2004年...浏览全文>>
-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学费一年多少钱】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是一所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本科独立学院,...浏览全文>>
-
【第一次点外卖的流程】对于第一次尝试点外卖的人来说,整个过程可能会有些陌生。不过,只要按照步骤来,就能...浏览全文>>
-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学费为什么要这么贵】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作为一所独立学院,近年来在学费方面引发了...浏览全文>>
-
【第一次登泰山的忌讳】泰山,作为五岳之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朝圣之地。对于第一...浏览全文>>
-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位于哪个城市】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是一所独立学院,隶属于首都师范大学。对于许多学...浏览全文>>